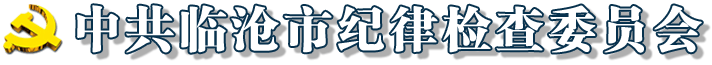吹鼓队作为民间艺人,在当今社会里很受人民群众的欢迎,但在过去地位却很低下。那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戏子王八锣鼓手”。当时社会把各行各业中比较低等的行业分为九类,吹鼓手与唱戏的、奏乐的、剃头的、衙役等都属于下九流行当,一般人家不得跟下九流的人联姻,下九人死后不得进入祖坟等。吹鼓手的头头叫“揽头”,做揽头的要必须掌握全面的吹拉弹唱技术或某一种出众的技术,要比较熟悉婚丧习俗。揽头和一般吹鼓手之间都是雇佣关系。
在过去,无论谁家办喜事都是要热闹一番的,其规模大小都是按办喜事主人的条件而定。一些比较富的人家都要讲大排场,喜主在结婚前先给“揽头”送单子,订时间人数,揽头按照喜主的需要通知吹鼓手。结婚前一天唱戏“响门”,吹鼓手唱戏是推拉俱全,但不走场不上妆,吹鼓手们也唱戏,全是高兴的调子,唱好了,观众会喝彩,喜主会给鼓手赏钱,赏钱与揽头无关,类似今天的奖金,吹鼓手得到赏钱后,一般要在观众面前谢赏。
结婚这天,新郎坐花轿去迎亲,吹鼓手要跟从。迎亲回来,场面更加热闹,花轿进了村子,前进的速度放慢,这时村里的男女老少都出来看热闹。吹手班的唢呐(分大铜,小号)笙、小镘等乐器齐呜,新郎新娘是按预定时间下轿的,时间不到,吹鼓手得一个劲的吹,也不向前走,这时,喜主就得赶快给他们赏钱,如果等的时间过长会赏好几次,吹鼓手就吹得越欢。夜晚,办喜事的人家,都是要在院场里烧起箐火,举行盛大的打歌仪式,这一天,前村后寨的人们都会赶来参与,吹鼓手们会做在一旁为打歌的人们助兴,众多村民就在激亢的锁唢声中,尽情欢笑尽情的跳。
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的吹鼓手一般是由几个年轻的吹鼓爱好者自由组合,没有了“揽头”。逢街房邻居的婚丧嫁娶,也都少不了他们,他们也乐意帮忙,事情结束他们也没要报酬。他们的名字也不再叫吹鼓手,而称“民间乐队”,有的乐器也换成了洋号,吹起来不像古时的大铜和小号那样费力。
在澜沧江畔一个叫朝阳寺的地方,有一群吹鼓的人们,这些平时在山中辛苦刨食的人、一群在黑土地上长大的面色黑拗的汉子,忽然间像天神似的顶天立地站在了大家面前,轻轻试了一两下音调后,双臂猛的一挥,大铜和长号齐唰唰的擎向天空,金黄的铜号和拴在铜号上鲜艳的红绸,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显得那般耀眼。
“轰……”一声石破天惊的巨响划破寂静的旷野,一股原始浑沌的神秘冲动和古老意念的混乱音符猛的从小号和大铜间窜出,通过音源传递直抵人们心灵的旮旯,使人有一种脱胎换骨般的快意。我们的双目被他们脸上肃穆的神情吸引,只见他们时而鼓紧腮帮,时而闭目轻吐,时而直抒胸意,吹出的间调柔时如丝稠无骨,坚时像枪击铜铁,乱时乌云横压,齐如布兵排阵,让人有入“铁马金戈乱箭飞,细雨轻风荷塘清,劈山开路是男儿,再闻堂前纺织声”之境,就在小号和大铜等乐器各种此起彼伏的声音中,我似乎听到了天神的意志,大地的精神,男人的粗旷,女人的娇娆,还有生命,婴儿呱呱落地的哭声,老人撤手西去的叹息……这些奇妙的幻象在各种乐器音调交织而成的罗网中,不断的冲突、纠结、呼啸、狂乱,直到鼓声嘎然而止。
面对着由这群敦实的山民制造的音乐奇迹,便想,作为民间一朵艳丽的少数民族文化奇芭,这些民间吹鼓队会一直传承下去,且愈演愈烈。(董琴)